
居易,乐天
作者:贺新郎
历观载籍,能属文者,官运大都不佳,如高适,贺知章,王安石之类,少之又少。当然,白居易亦在此列之外。
贞元十四年,白居易二十有八,高中进士。这次已是他再入长安了。
初来是以“野火烧不尽,春风吹又生”,如今再来,当是改换门庭,慈恩塔下的题诗,一如其人,压尽余下十六人。稚嫩褪去,豪情暗蕴。
史书再见乐天,已是六年后的元和元年。这一年圣恩赐了他一个周至县令,想来乐天对此应是不怎么满意的,除却未能与好友元微之同任拾遗补阙外,更多的,是对自己抱负难展的郁闷。
此年冬日,乐天好友王质夫、陈鸿邀其游雪,偶话起“太真旧事”,王质夫深表同情,遂陈鸿作传,白居易作诗,诗曰《长恨歌》。
提起《长恨歌》,便不免多谈几句。因白诗每伤啰嗦,且用词以老实著称,故而这篇歌行,显得尤为独到。开篇仅用四句,便省去陈鸿传中百字。用笔似刀切豆腐,精准利落。全诗明皇与杨妃二人的戏份基本做到分庭抗礼;前半段冷静客观,后半段又同情悲悯;或称白居易作此诗时,念及故乡佳人“湘灵”,以己喻明皇,湘灵喻杨妃。虽无考证,然余亦颇合此说。
周至的冬雪消融后,《长恨歌》与《长恨传》争相传唱,直至宪宗耳中。亦不知宪宗是如何读出了“惩尤物,窒乱阶,垂于将来”的意思,总之于元和三年,亲手擢白居易为左拾遗。
任上的白居易尽职尽责,作了许多讽喻诗。如《秦中吟》《贺雨诗》,再添上较前的《观刈麦》《卖炭翁》,也算开一代生面。但当这个时代真正需要他痛骂的时候,他却选择了“独善其身。”诗于白居易而言,或许只是器物。
乐天以杜子美为尚,甚至有“惟歌生民病,愿得天子知”之作,一如老杜“致君尧舜上,再使风俗淳。”但他穷尽一生,也没有成为杜子美。
元和五年,任上的乐天已经得罪了不少权贵,这一年的他请任京兆府户曹参军,“俸钱四五万,月可奉晨昏”。不知此时的他回看三年前“吏禄三百石,岁晏有余粮。念此私自愧,尽日不能忘。”又当是何感想?
明年四月,丁母忧。服阙三年,其入朝已是元和九年冬,帝授太子左善大夫。
元和十年四月,盗杀宰相武元衡,已除去左拾遗的白居易越职谏事。此前他因谏元稹左迁与吐突承璀兵事,已遭帝怨,加之任左拾遗时多提及“人之难言”之事,朝野树敌无数,这次终于遭到了权贵们的反扑。
此年秋,白居易左迁江州司马。其友元稹同年正月擢拔入京,四月却又被贬通州司马。元白二人素来情深,未曾想官运亦是同样糊涂。
此次贬谪,乐天已是四十四岁了。人至中年,心力渐衰,早年“兼济天下”的豪情,恐怕已经日渐消磨于黄芦苦竹旁的阵阵杜鹃声中了。
而在南下江州的途中,乐天遇到了那位二十五年前的白月光:“湘灵”,两人少年分别,至老相逢,湘灵为白居易终生未嫁,可此次再逢,白居易仍旧未娶。个中原因,人不得知。然若要深究,余窃以为平生狎妓三十二的白居易,恋的,只是曾经少女时的湘灵罢了。
又是一年秋,乐天因送客而偶闻京都琵琶声,问其身世,乃京城倡女,令其快谈数曲,一诉生平。作《琵琶行》以赠之。
《琵琶行》历来为人所道者,尽在其描摹声音之状。
“间关阴雨花底滑,幽咽泉流冰下难”
乐天此作,一如其人,抠抠搜搜。其少年家贫,供养颇多,故惟有为官可活家人。因而元和五年任官时,偏挑了“俸钱四五万”的户曹参军。其诗变化不多,贵在平实通俗,亦弊在平实通俗,难有李杜之雄丽险绝。其诗大多为自身影射,无论以何处出发,归根结底,总会在己身结尾。《琵琶行》中更是明目张胆,甚至琵琶女只是个供其回忆的器物而已。
《长恨歌》与该篇同为歌行,然《长恨歌》之布局捭阖,情思转换,十分大胆,处处彰显笔下劲力。何如《琵琶行》之力有未逮。
《旧唐书》载,乐天居江州时,“尤通释典,常以忘怀处顺为事,都不以迁谪介意”。但从其后来的诗作中,仍能看出他对绯袍的向往。
“那知垂白日,始是著绯年。”
四年江州的贬谪生涯,让曾经屠龙少年“愿得天子知”的豪情消磨殆尽,转而“宦途自此心长别,世事从今口不言”。
元和十四年秋,新帝即位,诏白居易还京,拜司门员外郎。越明年,转主客郎中,知制诰,加散朝大夫,官至二品,始着绯袍。同年,元稹诏还,知制诰,任尚书郎,同在纶阁。
元和十五年后的白居易,官越做越大,人却越耽越虚。
晚年的他用庄子和陶渊明的一些边角料为自己盖了一座心灵寓所,修成了世不关心的利己主义。庄子的坦然、陶潜的浑质,在白居易这里被扭曲成了一首首的自惜老朽,一番番的自甘平庸。
少年的热忱,中年的失意,或许都已沉溺在元和十一年秋天的浔阳江头。
秋风一吹,千年就这样过去了。后世的我们没有资格贬斥白居易如何如何,毕竟身处当时,你我定然远逊于白乐天。我们只是惋惜,一个理想主义者,终究妥协给了现实,故事里的屠龙少年,最终也变为了恶龙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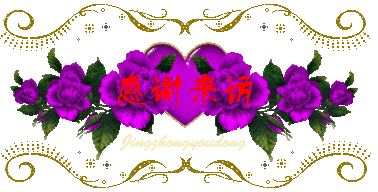

新长城文学网公众号

求索者文化传媒公众号
共 1 条评论
-

钓溪发表了评论
2023-03-01 18:26
亲,没有评论了春祺笔丰,遥祝好!